汪树东 || 点燃当代人的生态文明想象——当代中国生态散文发展综论
摘要:当代中国生态散文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9年的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20年的繁荣阶段。苇岸、胡冬林、杨文丰、艾平、古岳、傅菲等作家已经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当代生态散文家,以《大地上的事情》等为代表的生态散文集也给当代散文界赋予全新的生态意识。与西方生态散文相比,我国当代生态散文偏向于乡村田园情结,偏向于典型的人文精神,最终理想是天人合一,崇尚万物有灵。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更多当代作家转入生态散文创作轨道,必将创作出更多经典的生态散文。
关键词:生态散文;乡村田园情结;万物有灵;天人合一
“生态散文”是指以描绘自然或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主的、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的议论性或抒情性散文,不包括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因此像徐刚、李青松、古岳、陈启文等作家那些影响巨大的生态报告文学不在本文论述之列。至于所谓“自觉的生态意识”,刘军曾指出:“生态自觉包括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敬畏生命的写作伦理的确立,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视角,生物圈观念下的生命共享主义和平等精神。”其实,这无疑也是王诺所说的“生态整体主义”的题中之义。生态散文的形式较为自由,比较适合作家描摹万物、抒发胸臆、表达性情,为之者众,数量庞大。1978年以来的40余年间,生态散文家层出不穷,生态散文车载斗量,不可计数。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个作家写作散文时,能够从不涉及生态主题。翻阅新时期以来的每部散文集,都可以发现几篇旨趣相对纯正的生态散文,但是真正能够以生态散文名世,甚至专注于生态散文创作的作家并不多,卓然特立的主要有苇岸、胡冬林、杨文丰、艾平、古岳、傅菲等;对当代生态散文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作家则更多,主要有王宗仁、鲁枢元、周涛、李存葆、张炜、韩少功、陈应松、刘醒龙、迟子建、阿来、于坚、杨志军、郭雪波、鲍尔吉·原野、王开岭、周晓枫、刘亮程、王族、李娟、沈念、肖辉跃、安宁等。以单篇而言,王宗仁的《藏羚羊跪拜》、周涛的《巩乃斯的马》、张炜的《融入野地》、李存葆的《绿色天书》等都是声名卓著的生态散文;以文集而言,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艾平的《聆听草原》、傅菲的《深山已晚》、沈念的《大湖消息》等也蜚声文坛,影响深远。当代生态散文发展至今经历了萌芽、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呈现出与西方生态散文不同的精神旨趣和审美特色。本文拟采用宏观的文学史视野扫描当代生态散文的发展历史,勾勒出代表作家作品的基本特点,厘清当代生态散文的特征,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道路。
PART
一
当代生态散文的发展阶段
当代生态散文经过三个较为鲜明的发展阶段:1978—1989年的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20多年的繁荣阶段。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并不理想。一个方面原因是历史上的生态欠债,主要是革命意识形态长期倡导面向大自然的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生存哲学,罔顾生态规律,更谈不上尊重自然、敬畏生命。集体主义运动,加上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决策,往往更不会顾及生态规律;因此激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知青下乡”运动、“边疆建设”运动、持续高速增加的人口数量等等,都对全国的自然生态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资金和技术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往往也是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的。因此,最初的生态文学是以沙青、乔迈、麦天枢、徐刚、刘贵贤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为主,描绘了河流污染、森林残缺、动物灭绝等生态灾难;高行健的实验话剧《野人》批判的也是人们对神农架森林的破坏;阿成的《棋王》、孔捷生的《大林莽》、袁和平的《南方的森林》等小说则关注历史和现实中的森林破坏。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作家、学者对世界上的环保运动了解较为有限,对生态意识也不甚了了,主要精力放在反思“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伤害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翘首期盼上,他们普遍相信现代化意味着未来,意味着文明。不过,有少数作家凭着对大自然的敏感还是发表了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散文,例如孙犁的《黄鹂——病期琐事》(1962年创作,1979年发表)、汪曾祺的《泰山片石》、贾平凹的《读山》等,见证了当代生态散文的萌芽阶段。
此阶段值得关注的是张炜和周涛,他们对大自然的美极为敏感,较早孕生了生态意识,创作了生态散文。例如张炜在《葡萄园畅谈录》中就批判了当时人们对山东海边森林的滥砍滥伐以及化工厂的污染问题,他还认为作家应该是自然之子,有必要多亲近自然、融入自然,他对自己不太了解植物还颇为遗憾,“我们对植物所知甚少,简直可以说一无所知。……设想一下,你胸中储藏了五彩缤纷的植物形象,对它们有一个科学的理解,会怎样大地丰富你的思维。当写到它们的时候,你的笔力必然会更加坚实,更加准确和有力”。这几乎指明了张炜此后小说散文创作的一个主要方向。而周涛自从诗歌转向散文后,就创作了《巩乃斯的马》《二十四片犁铧》等典型的生态散文,“在对自然万物的充满激情的描摹中体现出美妙的生态意识”。周涛的《二十四片犁铧》对现代文明以暴力化的方式对待大地持严厉的批判态度,透显出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鲜明立场。不过,本阶段立意鲜明、风格独特的生态散文集还没有脱颖而出,专攻生态散文的散文家更是寥若晨星,生态散文的自觉发展还需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

《葡萄园畅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因发展经济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怨日盛;国际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日益影响到国内民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列;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思想文化也日益广泛地传播到国内,促进了国内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因此,越来越多的作家投身于生态散文创作中,代表性的篇章相继浮出历史地表,例如张炜的《你的树》《融入野地》《绿色遥思》、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韩少功的《遥远的自然》、鲁枢元的《为野草说情》、詹克明的《敬畏自然》、王英琦的《愿地球无恙》、李存葆的《鲸殇》、于坚的《山洞记》《大地记》、迟子建的《伤怀之美》等,艺术风格大相径庭,但均洋溢着亲近自然、融入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三部曲”(《灵魂像风》《西行阿里》《藏北游历》)中,也多有精美的生态散文篇章,表达了藏族人崇拜天地山川、敬畏自然万物的传统生态智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苇岸、张炜、李存葆、刘亮程等作家非常专注于生态散文的创作。苇岸受到海子、梭罗(Henry D. Thoreau)的影响,转向散文创作后便致力于生态散文。他言行一致,视野开阔,生态人格特质鲜明,对现代文明的生态反思较为彻底。他的《大地上的事情》《我的邻居胡蜂》《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等散文短小精粹,语言质朴,但生态立意高远,对随后的生态散文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炜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但是他的生态立场非常鲜明、坚定,他的《融入野地》高调展示了远离现代文明、融入荒野的生态立场,堪称当代文学生态转向的碑记之一;他对动物也非常关注,例如《美生灵》描绘羊的生命就极为动人,他的生态散文传达出了礼赞生命、敬畏生命的生态强音。李存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向散文创作,以极大精力投入生态散文创作中,《鲸殇》以开阔的视野描绘了近几百年来人类的捕鲸史,呼唤保护鲸鱼,保护大海,文字华美,想象瑰异,生态意识突出,极大地提升了生态散文的艺术境界。

《大地上的事情》,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4年版
新疆作家刘亮程在1998年推出了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一炮打响,甚至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乡村哲学家。《一个人的村庄》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生态散文集。刘亮程以鲜明的态度拒绝现代文明的驯化,回到村庄,回到大自然,倡导众生平等、万物有灵。这部生态散文集对21世纪之后生态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任林举的《玉米大地》、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雍措的《凹村》等散文集均深沐其思想艺术的恩泽。至于刘亮程对一个村庄的深度生态书写的创作姿态,更是影响了不少后来的散文集,例如张华北的《九秋:大洼生态散文》、黄孝纪的《八公分的时光》、吉布鹰升的《在凉山》、舒飞廉的《云梦出草记》等。
此阶段的生态散文出现了苇岸、刘亮程这样的标志性散文家,也出现了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这样标志性的生态散文集,但更多生态散文家、生态散文集的出现还要等到21世纪。
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间,生态散文明显进入了百花齐放的繁荣阶段。21世纪头十年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破坏加剧,各种天灾人祸相继爆发,民众越来越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到了第二个十年间,生态文明逐渐成为国家政策,民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渴望返回大自然,渴望亲近自然、融入自然。较有代表性的生态散文作家如周晓枫、艾平、胡冬林、杨文丰、李汉荣、傅菲、沈念、肖辉跃等纷纷涌现。
PART
二
21世纪生态散文的区域性特征
21世纪以来,因为不同作家处于不同的生态区域,生态散文创作也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较有代表性的是东北地区、内蒙古草原、新疆地区、青藏地区、两湖地区等。
东北地区的迟子建、素素、任林举、胡冬林等作家的生态散文较有代表性。迟子建的《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祭奠鱼群》《哀蝶》《黄沙蔽天时》《我的梦开始的地方》《是谁扼杀了哀愁》《假如鱼也生有翅膀》《我的世界下雪了》等都是较为典型的生态散文,或赞美自然生命,或反思小时候对待其他自然生命的残酷态度,或批判当前的生态危机,或表达融入自然的生态渴望,情怀朴素,文字洁美。素素的散文集《独语东北》中的《与鹤共舞》《绿色稀薄》《追问大荒》等篇章,对东北特有的丹顶鹤的描绘极为传神,对东北森林减少、野生动物消亡的生态问题也多有涉及。任林举的散文集《玉米大地》的生态书写则主要表现在那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关于人类对大自然竭泽而渔的破坏行为的描绘中。辽宁作家王秀杰和吉林出生的作家高维生多关注鸟类生活:王秀杰的《与鸟同翔》《水鸟集》《千秋灵鹤》《遥远的乡音》等散文集较为关注辽宁的鹤文化,关注自然生态的保护;高维生的“长白山野生飞鸟集”丛书之《天空流浪者》《鸟儿歌唱的地方》《寂静的森林》三部,多描绘长白山区的野生鸟类,兼具科普性和文学性,也是东北生态散文的重要收获。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吉林作家胡冬林的生态散文创作。21世纪以来,胡冬林曾多年到长白山深入生活,与大自然朝夕相处,融入荒野,践行着梭罗式的生活,最终写出了《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山林》《山林笔记》等重要的生态散文集,极大地拓展了当代生态散文的疆域。

《青羊消息》,吉林人民
出版社2004年版

《狐狸的微笑》,重庆
出版社2012年版

《山林》,河南人民
出版社2019年版
内蒙古地区的生态散文以鲍尔吉·原野、艾平、安宁等为代表,多关注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乌热尔图的《呼伦贝尔笔记》、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草木山河》、艾平的《长调》《呼伦贝尔之殇》《风景的深度》《草原生灵笔记》《聆听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郭雪波的《大漠笔记》等散文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典型的生态散文,都关注内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并尽可能地复活蒙古族传统生态智慧,张扬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生态意识。安宁则是近年来崛起于文坛的内蒙古散文家,她的散文集《草原十年》《寂静人间》《万物相爱》等,多呈现内蒙古草原上人与自然之间百转千回的情感关系,表达了作家尊重生命、渴望万物和谐的生态理念。
而新疆地区在21世纪也出现了不少专注于描绘新疆自然地理、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的生态散文家和生态散文集,较重要的有刘亮程的《在新疆》《大地上的家乡》、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永生羊》、李广智的《雪山·雪人·雪狼》、王族的《兽部落》《新疆密码:天山高原上的生存传奇》《神的自留地》、沈苇的《植物传奇》、康剑的《聆听喀纳斯》《喀纳斯自然笔记》《喀纳斯湖:一个山野守望者的自然笔记》、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遥远的向日葵地》《冬牧场》等。尤其是李娟的生态散文,以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眼光审视新疆大地,诗意丰沛、文字洁净,是周涛、刘亮程之后影响很大的新疆散文家。

《大地上的家乡》,译林
出版社2024年版

《我的阿勒泰》,花城
出版社2021年版
青藏地区的生态散文以杨志军、古岳、王宗仁、龙仁青等为代表。平措扎西的《世俗西藏》、杨志军的《远去的藏獒》、古岳的《谁为人类忏悔》《生灵密码》《棕熊与房子》、王宗仁的《藏羚羊跪拜》《藏羚羊的那些事儿》《可可西里的动物精灵》、龙仁青的《高原上的那些鸟儿》《高原上的那些花儿》、雍措的《凹村》等散文集,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上的生态问题,生态忧患意识鲜明,对青藏高原近几十年的生态变化做出了较为详细宏观的描述,对藏族人敬畏生命、众生平等的传统生态智慧做出了动人的勾勒与深描。其中,古岳的长篇生态散文《谁为人类忏悔》宏观描绘了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期青藏高原上森林、草原、野生动物、水土等生态变迁过程,视野开阔,生态情感饱满,震撼人心,堪称当代生态散文中的一个高峰。
21世纪华北地区的生态散文以周晓枫、阎连科、叶梅、李青松等为代表。苇岸的生态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周晓枫、冯秋子等人。周晓枫的《斑纹》《鸟群》《幻兽之吻》等散文或散文集知名度较大,已经确立了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能够从更为宏大的生态整体观角度来审视自然生命,她对各色动物素描般的描写也为当代生态散文增加不少光彩。她的生态散文具有典型的知性品格,注重生命哲理的感悟,情感内敛,具有一种鲜明的顿挫感、暧昧感,读来颇耐咀嚼、回味。冯秋子的《塞上》等散文集也像苇岸一样敬畏生命,礼赞自然。阎连科曾于21世纪初期在北京丰台区一个暂未被开发之地购得别墅,过上了与自然深度融合的诗意生活,表达了致敬陶渊明和梭罗的归隐田园的生态情怀,写出了散文集《711号园》。该散文集表达了非常明确的敬畏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意识,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对园中的动物、植物观察得非常精细,表达传神,例如《美国椿地下根须的争夺战》一文写美国椿地下根须惊心动魄的战争,可谓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最为生动特异的一幕。叶梅的散文集《福道》收集了作者多年行走于祖国大江南北创作的诸多生态散文,例如《鱼在高原》《福道》《神农架的秘密》《右玉种树》等。这些散文通过呈现生物多样性之美,强调唯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会有乡村和城市的天朗气清,人类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福道”,获得真正快乐幸福的美好生活。该散文集被评论家誉为“与自然对话的心灵之书”,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李青松近年来专注于生态散文创作,把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的笔法纳入散文中,笔姿多变,意趣横生。他的《另一种自然》《北京的山》《大兴安岭笔记》《哈拉哈河》等生态散文选材新颖,思考深入,情感丰富,对自然的描绘极为精美。他的散文集《相信自然》《北京的山》较好地呈现了作者相信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

《711号园》,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版
至于梁衡的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则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梁衡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在《树梢上的中国》中讲述了不少古树背后的人文历史,例如《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讲述左宗棠在甘肃种植柳树的故事。不过虽然该文集在文坛上、社会上影响较大,但是若从生态散文角度看来,因为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叙述人文历史,而不是关注生态问题,生态意识也并不鲜明,所以该文集不能被视为真正的生态散文集。之所以在此提及,是为了回应社会上的普遍误解。河北作家刘向东的散文集《动物印象》把最丰沛的情感倾注到蜻蜓、蝉、猫、鸟等动物身上,把作者幼年时对动物的各种印象汇聚一堂,加以生态视角的重新审视,写来意趣盎然。河北作家张华北的散文集《九秋:大洼生态散文》关注河北沧州大洼湿地的生态问题。河北作家冯小军的散文集《裁一片绿影送给你》写出了一个务林人对森林的文学审美、对森林与人的生态关系的深层思考,彰显了务林人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牺牲精神。山西作家玄武的散文集《物语者:动物风度与人性本色》在对各种动物的书写中体现了尊重生命多样性的生态意识,散文集《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则被称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自然观察笔记”,观照自然细致精微,多从人与植物的生态关系入手,对作者所处地方的生态变迁多有述说。

《种花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华中地区的湖北、湖南在21世纪生态散文创作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湖北作家的生态散文魏紫姚黄,绚丽多姿,渐成风景。熊召政从21世纪以来始终倡导重建诗意的生活,倡导保护环境,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智慧。他认为生态是长江的血液,而文化是长江的灵魂,要保护好长江的自然生态,否则长江文明就会丧失根源。他的散文集《踏遍青山人未老》中的文章多是他走遍大江南北后的产物,蕴含着对大自然极深的感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随处可见。刘醒龙近年来在《上上长江》《婆娑大地》等散文集中对自然生态问题多有描绘和反思,他赞美大江大河壮美的风光,也强烈批判山河遭到的生态破坏,对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大加赞赏。陈应松在散文集《朝向一朵花的盛开》中倾听大自然,唤醒灵魂深处的宁静,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大爱无疆的生态智慧,其中《神农架之秋》《神农架云海》《诸神充满神农架》等篇章描绘神农架的自然之美,文采纤秾,情感富丽,令人沉醉。刘诗伟则在散文集《人间树》中写他的故乡江汉平原一个小村庄兜斗湾中人与树之间的故事,凸显了树在乡村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而礼赞了自然之大道。华姿的散文集《万物有灵皆可师》聚焦于种种自然生灵,宣扬万物有灵、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生态意识。华姿的生态视野较为开阔,关注的自然生命既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蚂蚁、蚯蚓、屎壳郎、麻雀、水稻、鸢尾花等动植物,也有生性独特、遥远异国的动植物,例如袋鼠、小象鼩、驯鹿乃至大白鲨等。她对所有自然生灵都怀着一种耶稣基督般的慈爱,赞美它们的生命之美,尊重它们的内在价值。此外,舒飞廉的散文集《云梦出草记》则聚焦于湖北孝感肖港镇郑家河村的草木,洋溢着乡村草木气息。湖北作家的生态散文描绘的多是四处旅行时的自然审美经验,或是对故乡自然的回顾式凝望,而很少像梭罗的《瓦尔登湖》那样对一个特定的地方展开生态细察和审美深描。

《踏遍青山人未老》,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23年版
21世纪湖南生态散文则以韩少功、学群、沈念、肖辉跃等为代表。韩少功渴望过上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乡村生活,于21世纪初期回到了湖南汨罗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深度融入大自然,后来出版了他的长卷散文《山南水北》,共收散文99篇,其中许多篇章如《耳醒之地》《感激》《养鸡》等,特别呈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自然生命的诗意观照,是难得的生态文学佳作。学群受到梭罗、约翰·缪尔(John Muir)等的影响,也具有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著有散文集《生命的海拔》《两栖人生》《牛粪本纪》等,其中不少生态散文关注洞庭湖地区的生态问题。例如《草和芦苇的宗教》批判洞庭湖边的捕鱼、猎鸟等陋习,表达了对自然的皈依之情;《螺蚌世家》表达了悲悯众生的护生意识;《通往自然的驿站》则似乎是对梭罗《瓦尔登湖》的深情回应。沈念的散文集《大湖消息》关注湖南洞庭湖的生态变迁,是对地方生态的诗意表述,其中《大湖消息》讲述的是洞庭湖地区人与野鸟的关系,毒鸟和护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生态观念;《麋鹿先生》则关注洞庭湖地区野生麋鹿的放养和守护;《故道江豚》讲述了洞庭湖地区江豚的保护事业;《黑杨在野》则讲述了洞庭湖地区因经济原因造成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这些散文多采用小说笔法,悬念迭起,生态意识明确。肖辉跃于2019年出版生态散文集《飞越高原》,因对鸟类的热爱、守护、追寻、描绘和摄影而被誉为“三湘第一女鸟人”。但随着年岁渐长,她于2016年再次重返故乡湖南宁乡,沿着靳江流域展开博物学、生态学之旅,持续三年多,并最终把关于故乡生态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汇聚为生态散文集《醒来的河流》。该散文集聚焦于作者数年乃至数十年对靳江流域(宁乡段)的自然生态尤其是鸟类生态的观察所得,呈现了生动活泼的乡村生态图景,展示了作者热爱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态伦理,建构出独特的乡村生态审美视域,从而极好地推动了当前生态散文的发展。除这些代表作家作品之外,湖南作家谢宗玉的《村庄在南方之南》《草木童心》、黄孝纪的《八公分的时光》、黄亮斌的《圭塘河岸》等散文集也颇有自觉的生态意识。

《醒来的河流》,商务
印书馆2023年版

《生命的海拔》,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1世纪江西生态散文作家以傅菲、范晓波、罗张琴等为代表。傅菲是近年蜚声文坛的散文作家,也专注于生态散文创作,他的《深山已晚》《鸟的盟约》《灵兽之语》《客居深山》《野禽记》等散文集,多聚焦于赣东北的山林田园,以诗意笔触描绘融入自然的生态境界,善于化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文笔流丽,构思精巧。傅菲的“饶北河系列”和“大自然系列”散文是最富有生态意识的。傅菲已经构筑了敬畏生命、众生平等、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以诗意笔触为读者描绘出或质朴或绚丽的自然之美;他也关注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亲身实践惜生护生的生态伦理,屡屡严厉批判现代人对自然生命的残害;他还自觉接受华夏古典诗词的美学浸润,接受美国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等生态作家的深刻影响,试图建构一种人文与自然、写意与写实、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山地美学。他的生态散文对推进当代生态散文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范晓波的散文集《田野的深度》多记述江西各地的自然风物和民情风俗,对那种人与自然融合的乡村景观的描述颇为动人,透显出一定的生态意识。罗张琴的散文集《鄱湖生灵》关注江西鄱阳湖区的自然生灵,选取了藜蒿、芦苇、鹤、江豚等鄱阳湖畔具有特殊习性、诗意象征、文化传承的动植物,融入了作者丰沛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再加上踏实的田野调查,人文情怀和生态意蕴相得益彰。
除了以上地区较为集中出现的生态散文作家、作品集之外,其他地区还有不少较为优秀的代表作家、作品集。如陕西作家白忠德的《大熊猫:我的秦岭邻居》《生态秦岭动物趣》《秦岭的动物朋友》等散文集,多关注秦岭的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野生动物,体现了人类对动物的热爱,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陕西作家李汉荣的散文集《万物有情》以万物有灵式的眼光打量山川大地、草木生灵,写出了人与万物之间的美好情谊,散文集《河流记》则从作者的切身经验中写出了大地伦理和河流美学,《动物记》《植物记》等散文集也颇多富有生态意识的美文篇章。

《深山已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万物有情》,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2019年版
山东作家李存葆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散文创作势头,继续拓展新的生态题材,创作了《绿色天书》《最后的野象谷》《净土上的狼毒花》《神农架启示录》等脍炙人口的生态散文,篇幅较大,情感饱满,影响巨大。山东作家王开岭的散文集《古典之殇》的副标题是“纪念原配的世界”。所谓原配的世界就是大自然还比较纯净、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世界。他深受古典诗词的山水自然精神的影响,再加上梭罗的《瓦尔登湖》、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的《自然的终结》、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的《哲学走向荒野》《环境伦理学》等书的影响,最终确立了自觉的生态意识。因而他的《再见,萤火虫》《蟋蟀入我床下》《河殇》等文或批判现代文明对大自然的残害,或表达对“原配世界”的大自然的真诚怀念。山东作家周蓬桦的散文集《大地谷仓》用简洁明亮的散文语言,以个人化的投入姿态深入故乡、森林与草原,行走或静思,体察生灵与自然伦理,呈现个人命运与万物共情的价值思考。
作家杨献平曾在巴丹吉林沙漠从军生活多年,对该地的自然生态较为了解,著有“巴丹吉林沙漠文学地理”之《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沙漠的巴丹吉林》等散文集。其中,散文集《沙漠的巴丹吉林》书写了瀚海之中的沙尘暴、辽阔戈壁、孤立的牧区,以及黄羊、蜥蜴、蝎子、四脚蛇等诸多沙漠动物,对沙漠生灵的描绘活灵活现,是当代生态散文中不可多得的关于沙漠生态之篇章。
江浙地区的生态散文作家以庞余亮、周华诚等为代表。江苏作家庞余亮的散文集《小虫子》写蜜蜂、蜻蜓、萤火虫等各种小虫子,充满了童趣、虫趣,被誉为“中国版《昆虫记》”。而浙江作家周华诚的《草木滋味》《草木光阴》等散文集有意远离城市,返回乡村和自然,重归田园,倡导一种悠远缓慢、古典式的生活美学。华南地区的生态散文作家以林宋瑜、蒋子丹等为代表。广东作家林宋瑜的散文集《蓝思想》关注广东东部沿海一带近几十年的滥伐红树林、围海造田、围海养殖等造成的沿海生态破坏,选材独树一帜,令人印象深刻。蒋子丹对城市里的宠物问题较为关注,特别创作了《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和《动物档案》两部散文集,思考动物权利、动物保护问题,也属于别出心裁的生态散文。

《草木光阴》,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8年版
21世纪生态散文发展过程中,有不少自然科学出身的作家,受过严谨的科学训练,培育出鲜明的生态意识,再投身于生态散文创作,别有特色。上海作家詹克明是核物理学家,他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路子,相继出版了《空钓寒江》《青梅嗅》两部散文集,把科学家的冷静理性和作家的热情想象结合得丝丝入扣,继续倡导敬畏生命、批判生态危机的鲜明立场。而广东作家杨文丰出身于气象学专业,于21世纪投身生态散文创作,以《自然笔记》《病盆景》《雾霾批判书》《海殇后的沉思》《走进子宫式生态圣殿》《不可医治的乡愁》《精神的树,神幻的树》《人蚁》《佛光》《心月何处寻》等篇章极大地拓展了生态散文的思想深度。陕西作家祁云枝供职于陕西省西安植物园,从事植物学研究,近年来出版《我的植物闺蜜》《低眉俯首阅草木》《草木祁谈》《植物,不说话的邻居》等科普散文集,重拾现代人失落的草木情缘,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语言清丽,值得一读。郭耕长期关注动物保护等事业,也曾创作了《天地狼心——郭耕自然科普随笔》《鸟兽悲歌》等科普随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21世纪生态散文作家中还有不少作家建立了难能可贵的博物学视野,在对植物、昆虫、鸟类等自然生命的田野观察中达成了极好的文学审美,从而创作出系列生态散文,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河南作家祖克慰的《观鸟笔记》《动物映象》、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云南作家半夏的《与虫在野》、重庆作家李元胜的《旷野的诗意: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浙江作家津渡的《我身边的鸟儿》《草木有心》等散文集,新鲜别致,清新动人,把自然生命的倩影移入散文世界,增添了生态散文的绿色气息。王兆胜曾说:“真正在万物描写上倾注心力的生态散文还是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散文家全力以赴写‘物’,努力展现‘物性’的光辉,从而在规模效应、体系化、专业知识化程度上都有质的飞跃,特别是作家的生态散文物性书写具有了博物学、生物学、动物学、民俗学、地域学的特色。”应该说,像半夏、李元胜这样的作家在生态散文创作中就极好地呈现了博物学的物性书写。
PART
三
当代生态散文的社会影响与特征
当代生态散文发展至今,社会影响已经渐渐增大。最初大多反响寥落,到如今许多篇章早已声名卓著。有不少典型的生态散文已经被收入到中学语文教材中,例如王宗仁的《藏羚羊跪拜》、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与《我的邻居胡蜂》都已经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至于张炜、杨文丰、傅菲、学群、李汉荣等人的生态散文更是屡屡出现在中学语文考卷乃至大学语文教材中。更为直接的证据是不少生态散文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奖。例如周涛的《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李存葆的《大河遗梦》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刘亮程的《在新疆》、周晓枫的《巨鲸歌唱》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沈念的《大湖消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此外王充闾的《春宽梦窄》、素素的《独语东北》、郑彦英的《风行水上》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中也颇多典型的生态散文篇章。

《在新疆》,江西人民
出版社2017年版

《遥远的向日葵地》,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
吴周文曾说:“中国生态文学与生态散文思潮的发生,与中国读者接受《沙乡年鉴》《瓦尔登湖》等外国生态散文的思潮密切相关,《沙乡年鉴》等外国思想资源是先导的,中国生态文学对它的接受,则是十分自觉的。”的确,当代生态散文的发展是受到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思想较大影响的,尤其是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对中国作家和生态散文的影响特别深远。苇岸曾被誉为“中国的梭罗”,他从事生态散文的创作就与梭罗《瓦尔登湖》的影响有关。张炜、韩少功、刘亮程、詹克明、王开岭、学群、傅菲、黄亮斌等人都受到梭罗的巨大影响。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阎连科的《711号园》、严风华的《一座山,两个人》、丁燕的《沙孜湖》、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胡冬林的《山林笔记》、黄亮斌的《圭塘河岸》等散文集都被誉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此外,蒋子丹比较喜欢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鲁枢元、王开岭都充分接受了罗尔斯顿的荒野伦理学,傅菲、龙仁青、肖跃辉等受到约翰·巴勒斯的巨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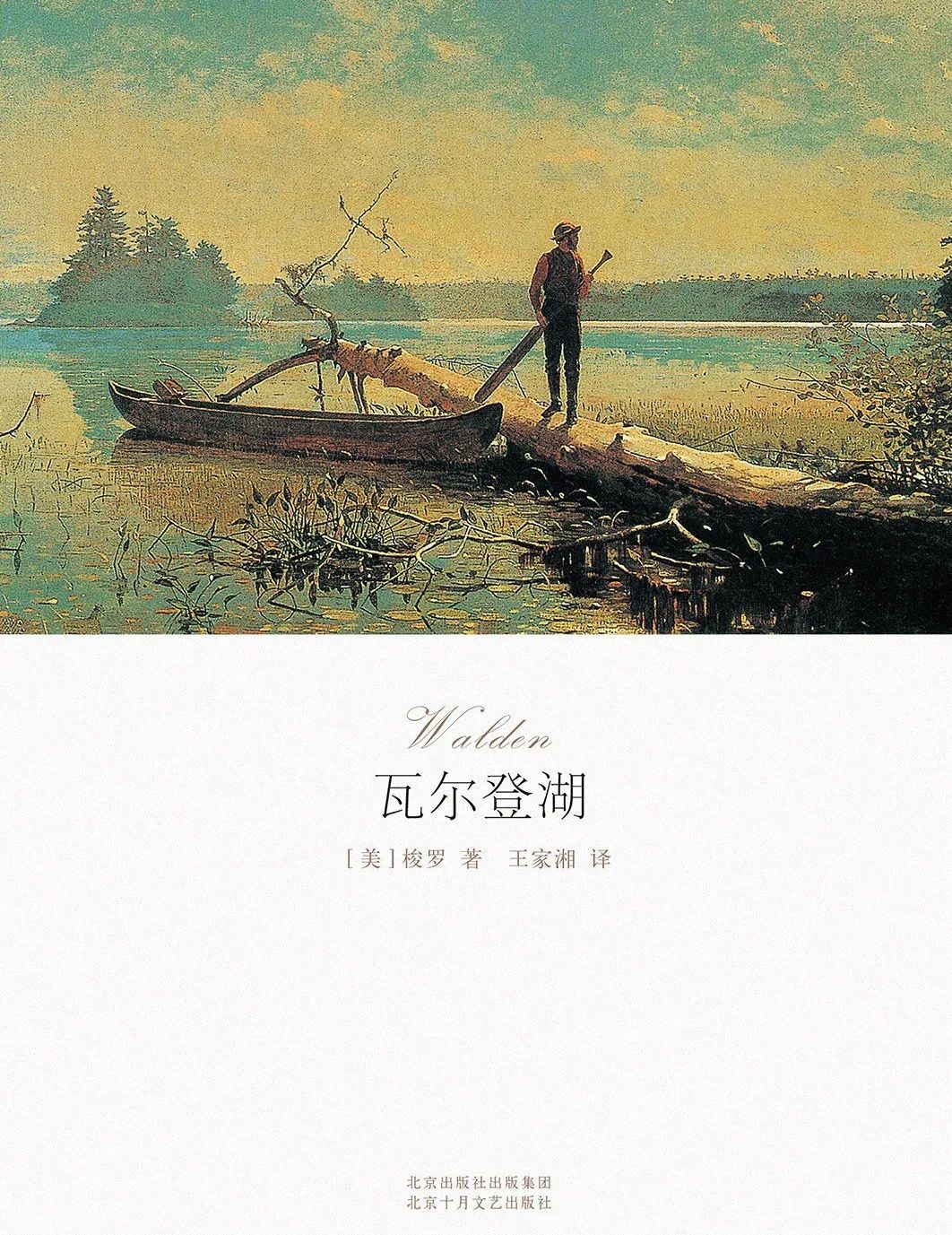
《瓦尔登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
当然,如果整体观照中西当代生态散文,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较为鲜明的差异。首先,中国生态散文偏向于乡村田园情结,而西方生态散文偏向于荒野情结。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影响至为深远,若说我们寻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也是寻求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天人合一,是对荒野的改造,是远离虎豹豺狼等猛兽,也远离荒榛野莽,最好的表达便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绝大多数中国散文家要表达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旨趣,亲近、融入的是已经被人为改造后的乡村田园,是风和日丽、山明水秀、梅兰竹菊、鸢飞鱼跃的。到了当代生态散文中,这种乡村田园情结依然是支配性的,例如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任林举的《玉米大地》、傅菲的《深山已晚》、范晓波的《田野的深度》等,都是乡村田园情结的自然流露。以傅菲、谢宗玉、周华诚等代表的生态散文则可以视为从乡土散文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支脉。
与之相对,欧美散文的生态书写往往偏向于荒野情结。梭罗的《瓦尔登湖》便明确展示出回归荒野的精神旨趣,他惊世骇俗地认为荒野里才蕴含着世界最后的救赎。此后,绝大多数倾向于生态书写的散文家无不以梭罗为精神领袖,向着荒野挺进,例如约翰·缪尔、约翰·巴勒斯、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等便是典型例子,巴里·洛佩兹甚至到北极去寻找真正的荒野。不过,随着中国人的视野日益开阔,文化胸怀日益丰厚,尤其是现代化浪潮日益侵蚀,使得原生态的大自然日益稀少也日见珍贵,也有不少作家开始关注荒野,偏向荒野,例如张炜、古岳、杨志军、胡冬林等作家就是如此。
其次,中国散文的生态书写偏向典型的人文精神,而西方散文的生态书写则偏向典型的科学精神。一般而言,中国作家接受的多是人文主义教育,古典作家多浸润于儒、道、佛的思想中且不说,即使当代作家也多是与文史哲耳鬓厮磨,而少有作家能够兼得自然科学的耳提面命。因此当作家关注自然、关注生态时,他们多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胜景的憧憬开始,批判生态破坏,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但是他们缺乏对大自然的严谨细致、持之以恒的观察与研究,也缺乏对大自然的生态智慧的科学考察。他们的生态智慧多来自先哲的启示,来自切身的生活经验,来自民间的生活智慧。与之相较,西方作家关注自然、关注生态,倚重的是严谨系统、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许多生态散文家往往就是非常成功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对塞耳彭自然的细致考察,法布尔对昆虫的观察和研究,梭罗对缅因森林的生态考察,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对沙乡生态的研究,爱德华·艾比、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等对沙漠的观察与研究,巴里·洛佩兹对北极的生态研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对杀虫剂、海洋生物的研究,等等,都是远近闻名的例子。他们的生态智慧更多来自长期的实地观察和科学研究,因此他们的生态书写具有较为典型的科学性、客观性、真实性。当然,随着西方生态散文的影响逐步扩大,也有不少中国作家开始学习西方作家的那种踏实勤谨的科学精神,认真细致地观察与研究大自然,发而为文,也显示出卓然不凡的科学精神,例如李元胜、半夏对昆虫的观察与书写,胡冬林对长白山的生态观察,古岳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的实地调查,等等,都是令人敬佩的典型。至于詹克明、杨文丰、祁云枝等具有科学背景的作家加入生态散文创作队伍,更是增添了生态散文的科学精神因子。
再次,中国散文的生态书写最终的理想是天人合一,而西方散文的生态书写多是与大自然保持适当的观察和审美的距离。也许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实在太过巨大,中国作家在关注大自然、关注生态问题时,表现的理想情境都是天人合一的胜景。他们渴望亲近自然、融入自然,渴望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中安顿身心、怡情养性,认为只有融入大自然才能解决人生的悬浮无根状态,才能超越人生的孤独,才能获得终极意义的实现。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国作家而言,大自然的确具有教堂、信仰之于西方人的那种救赎意义。也正是因此,中国作家普遍对大自然的溃败、对生态危机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愤慨。没有大自然的青山绿水、鸢飞鱼跃,所有人类物质财富构筑的世界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无法安居的,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中国散文的生态书写中,最美的境界都是描绘天人合一之境的。
相较而言,西方作家在书写大自然、书写生态时,始终保持着一种较为冷静的距离感。他们观察大自然,思考大自然,也反思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主体性极为鲜明,他们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融入大自然中。因此,阅读西方生态散文,我们可以随时感知到作家的主体人格形象。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西方散文的生态书写中完全没有天人合一的生态体验书写,无论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是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中都有一些片段描绘天人合一的生态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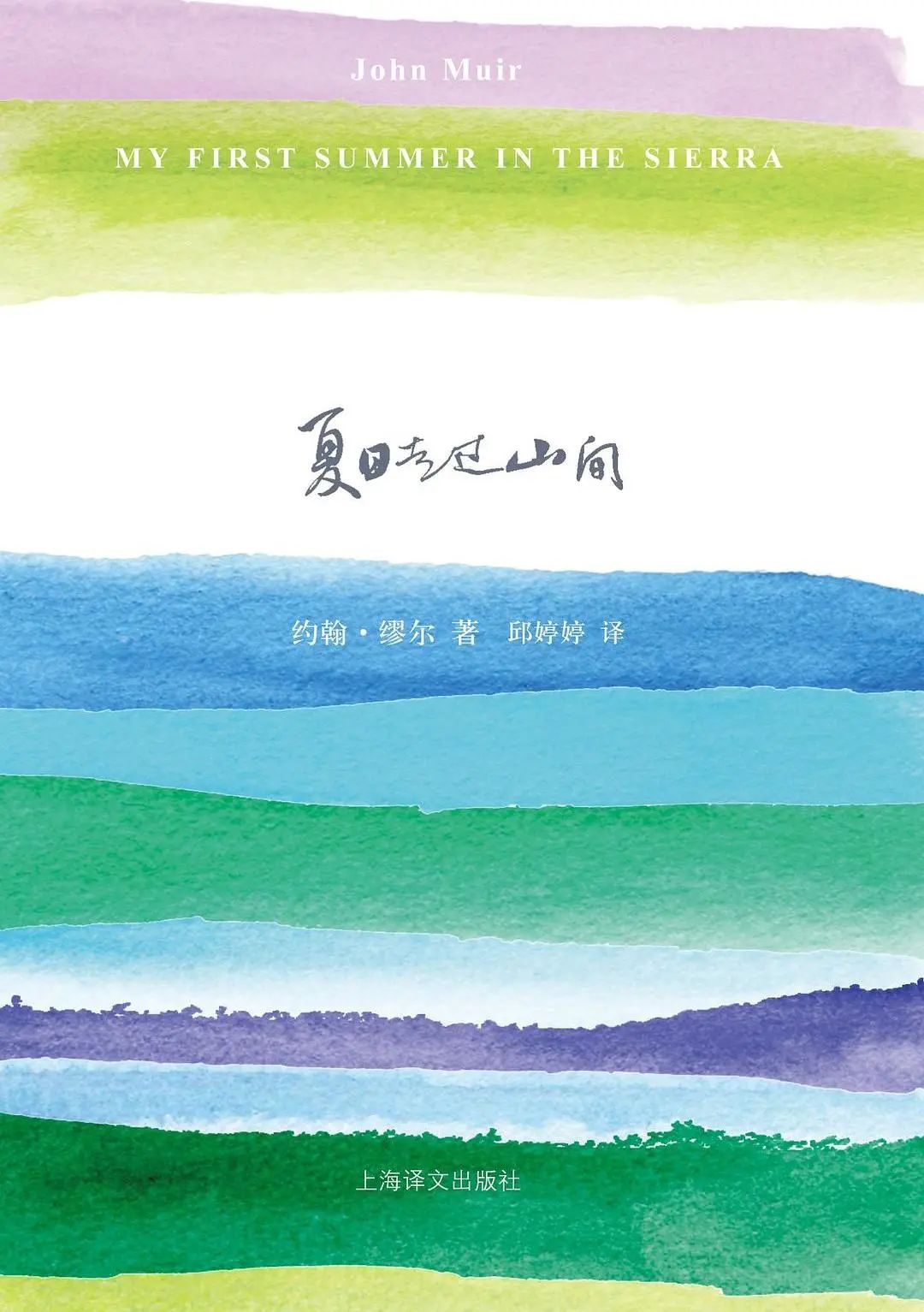
《夏日走过山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版
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万物有灵论对中国散文的生态书写影响较大,但是对西方散文的生态书写影响却稍逊一筹。所谓“万物有灵论”,是相信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灵魂,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万物也会以灵魂影响到人的世界。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中曾认为宗教信仰起源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对现代人,尤其是具有科学精神的现代人影响甚微,但是对于那些还保存着祖传信仰的少数族裔而言,影响依然在延续。对于中国作家而言,首先是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保存着对万物有灵论的深切记忆,例如藏族作家古岳、雍措,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满族作家胡冬林,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仡佬族作家潘琦,等等,都较为信奉万物有灵论。当然,还有些汉族作家,如张炜、迟子建、刘亮程等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给中国散文的生态书写带来了较为神秘的本土化色彩。与之相对,西方作家在书写自然、书写生态时,很少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相信人的灵魂,但不会承认自然生命也有灵魂。他们欣赏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生命,乃至敬畏自然生命,但不是出于人的灵魂和万物的灵魂的交往互动、彼此感应,而是人的灵魂力量的扩展、外射。
PART
结语
整体看来,生态散文已经在当代散文发展中渐渐形成一股潮流、一种气势,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类型存在,在散文百花园中卓然独立,摇曳生姿。张炜、韩少功、陈应松、李存葆、苇岸、胡冬林、杨文丰、艾平、古岳、傅菲等生态散文家早已经成为当代散文界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作家。至于《大地上的事情》《绿色天书》《一个人的村庄》《山南水北》《谁为人类忏悔》《711号园》《聆听草原》《流水似的走马》《山林笔记》《深山已晚》《大湖消息》等生态散文集在当代散文界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与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法布尔的《昆虫记》、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世界经典的生态散文集相比,我国当代生态散文还略显稚嫩,尚没有提出原创性的生态思想,艺术性也略逊一筹。此外,当代生态散文也存在着模式化、标准化的弊病。刘军在《以大山的方式理解森林——关于“生态散文”的边界思考》一文中还提出生态散文创作除了要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之外,还需要田野经历的加持、系列写作的托举。笔者认为这也是切中肯綮的建议。但是笔者相信,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散文家不由自主地进入生态散文创作的轨道,更具创造性、更经典的生态散文必将浮现于地表,进一步绿化中国文学,启蒙读者的生态意识。王兆胜曾说:“中国式生态散文应吸收西方生态文化、理论、文学、散文的精华,摆脱其坚硬的外壳,用中国精神、中国心灵和中国智慧使之发出更耀眼的光彩。”的确,中国式生态散文必须具有独特的中国光彩,那样才能与其他各国生态散文交相辉映,共同点燃当代人的生态文明想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散文研究”(22BZW169)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5年第2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汪树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学,20世纪中外文学。主要著作有《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中国散文中的生态智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