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琳 || 字里行间散发着人性真理幽微之光-读肖勤中篇小说《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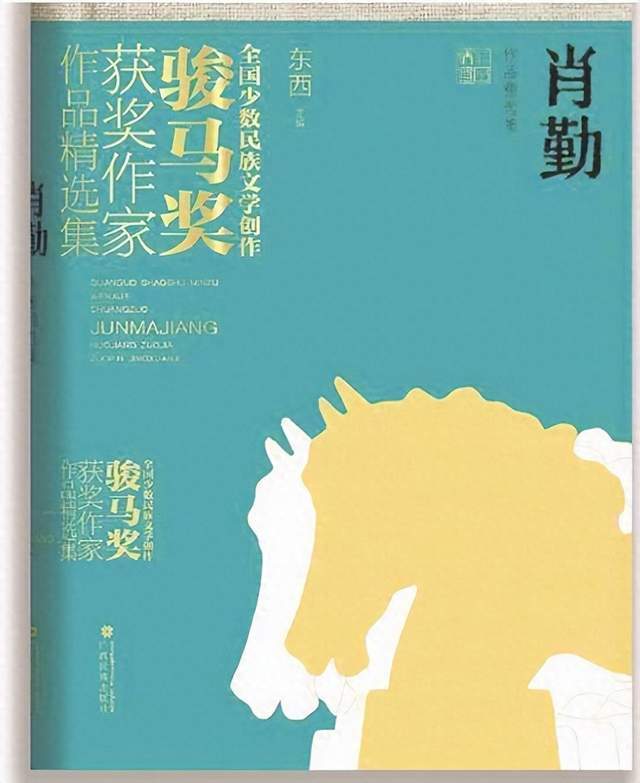
字里行间散发着人性真理的幽微之光——读肖勤中篇小说《暖》
作者:胡明琳
仡佬族作家肖勤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性作家。虽说接触其作品的时间不长,但凡读过的小说和散文我都喜欢,尤其是她的中篇小说《暖》。
《暖》曾在2011年3月荣获第二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改编的电影《小等》也在2012年上映后,获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长篇奖”。
小说描写了12岁的留守女孩小等独自照顾年迈多病的奶奶,一边用稚嫩的肩膀挑起农活和家务的重担,一边在孤独苦中等待在外务工的母亲归来的故事。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探讨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情感教育问题。之所以与《暖》共情,或许与我的留守经历有关。小等的诸多感受就是儿时我的感受:十岁的大姐带着七岁的我在村里独自生活,姐俩那些相依为命的岁月就是小等和奶奶的岁月,小等的形象就是大姐的形象,也是村里其他“小当家”的形象。
“留守儿童”这个术语虽说是2016年3月公安部、民政部、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关于留守儿童的摸排工作时首次给出官方的定义: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过这一说法在官方语境的使用可追溯到2010年,没有这一说法但事实已经存在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和年代。要知道,在出现打工潮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村庄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一老一小孱弱地面对生活的诸多困境,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情感教育和爱的缺失。而当时作为乡镇干部的肖勤来说,正亲历了关爱留守儿童、关爱务工人员和关爱空巢老人的“三关工程”,于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艺术化地再创造了《暖》的文学世界。
作为现实题材的作品,与同一时期书写留守儿童的作品《天赐》《念书的孩子》等不同,虽说都是写苦难,《暖》却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作者笔下的文字散发着人性真理的幽微之光,如黑暗中的火花,闪烁着希望。
一、朴素的审美理想
中华文化多以至善(好,圆满、良善)的追求为核心价值,强调善美相兼。而肖勤的作品中,无论经历多大的苦难,都没有否定生命中那些一定存在的善意,哪怕是点滴的,微不足道的。
我们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没少见那些偷奸耍滑的、黑心肝村干部形象,然而《暖》中肖勤塑造的村主任周好土却非常温暖,正义。虽说他的语言和他的名字一样土,但也一样纯良。在卖辣椒那个人潮拥挤的现场,眼角扫见小等被背筐压弯得只留个头,周好土赶紧走上去搭手接下筐。“你妈寄钱了吗?还是不回来?你奶奶好点没?”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递给小等:干净的,擦擦汗。看到辣椒贩子短小等的斤两,他顺手从身旁的辣椒篮里抓了把灯笼椒甩进小等的筐里,对椒贩子一脸不耐烦:几千几万都敢赌,到这里为一毛钱和小姑娘吼,也不嫌丢人,还四舍五入,给,够你入了。一个正直的,接地气的村干部的样子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
在肖勤的笔下,人民不是抽象化的、虚化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爱憎分明的。《暖》中除了小等这样的典型人物外,村主任周好土、乡村教师庆生等中间人物的塑造也非常成功,两个中间人物的动作和语言,主导了文中暖的基调,给小等寒冷的生活照进一丝丝光亮。
周好土勉强收下小等家的罚款后,从自己裤兜里拿出了五块钱对小等说:没吃中饭吧,去,吃碗绿豆粉再回去,顺便给你奶买把面条。小等直摇头:我家和你有仇,我不能要你的钱。
脸上还带着小等奶奶留下抓伤的村主任周好土既埋怨小等母亲对孩子和老人的不管不顾,又心痛小等的无依无靠。这种朴素豁达的情感,多么质朴。说明作者内心觉得:光明比黑暗更值得歌颂。看到这些中间人物,我也会想起我与大姐留守在家时,农忙时帮我家犁地的龚表叔,我在很多散文里都描写过他。他帮我们家犁了一天地拖着满身的饥饿和疲惫回来之后,看到村里的孩子都去邻村看露天电影去了,为了不耽搁我和姐姐也去看电影,他水都没喝一口,就一声不吭地扛着犁头回家去了。要知道,他去别家帮忙,人家可是要好酒好肉招待的。这些质朴的中国农民形象,正是我们写作者需要书写的,作者肖勤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人物的闪光点。
二、节制的情感表达
在文艺批评实践中,既强调文艺作品所蕴含的思想纯正,合乎礼仪,又强调在语言形式表达上要中正平和,文质彬彬。孔子高度评价了《诗经》的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回顾《暖》一文,中和之美也用得恰到好处。就拿晚上奶奶发病,小等不敢一人在家,躲到半山腰庆生老师家去寻求帮助来说吧!“这是在谁怀里?真舒服!小等皱皱眉毛,想睁眼却睁不开,眼比石头还重。是妈妈的,一定是,小等想原来我是在做梦,那千万不能睁开眼,一睁眼妈妈就不见了!”当她晕倒在庆生怀里醒来时,作者从孩童的视角表达出了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孤独太久了,渴望母亲的怀抱,渴望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于是她闭着眼,不想睁开,又怕这一切都是梦,醒来后变成一场空。
小等向庆生诉说了奶奶疯癫的症状后,她一把拉住庆生的手,老师我不敢回家,让我在你家睡吧,我好多天没睡觉了,我困。
庆生为难地说老师一个人,你住这儿不方便。小等急忙说我白天可以帮忙做饭抵房租。女孩根本不知道庆生老师说的不方便指什么。她渐渐长大,男女有别,这些知识没人教她。听了小等的话,庆生的心“潮湿”起来,他温和地问:小等几岁了?十二岁。十二岁是大人了,就不可以在老师家睡。这样的提醒,本应该是母亲的责任,结果却由庆生这个身体残缺的单身汉告诉她。
小等和庆生的相守相依的过程,作者没有任何的议论和价值评判,只有场景的描述:庆生洗脚时,小等赶紧提着保温瓶和大狗老黑一起蹲在脚盆边,隔一会儿便往里兑热水,直泡得庆生麻木的跛腿透气提神的泛出红光才罢休。作者打破了世俗的眼光,描绘了一幅幸福而又温情脉脉的画面。庆生的人物形象我觉得塑造得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的度,他行为的度,思想的度,语言的度都体现了他内心的美好。包括他对某个念头的自责,对周好土骂他后的下跪,都反映了他的真实与善良。
读完《暖》,我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为小等,为庆生老师,为他们的孤独无助,为其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读完这部小说,令你不忍心去责备任何人,哪怕是小等的母亲,再婚的她面对新的家庭,新的责任也有她的无奈。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文学的力量,我们的情绪跟着文中的人物起伏跌宕,时而害怕,时而伤心,时而又充满期待。小等缺少一个温暖的家,庆生渴望有一个家。哪怕在文本的最后,面对现实的无奈,小等触电身亡的那一刻,都是带着对母爱的渴望而走的,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都是伴着美好的幻想而走。正是作者这些凝练节制的语言和温情的表达,提升了文本的审美境界。
二、传神的语言艺术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文学的形态在于以其富有文采的语言进行文化修辞表达。刘勰说:若气无奇类,文乏异彩,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
肖勤的文学语言很有辨识度,浓郁的黔北乡音妙语连珠,自然得就像从大娄山流淌出的山泉。特别是那些形象的比拟快速把读者带入典型场景。
“夏天的大娄山脉,太阳是有年龄的,清晨的太阳是吃着奶的娃,饱满嫩白的光芒像娃儿胖乎乎的小肉手,甜滋滋、温嘟嘟贴在人身上和脸上,小等拍拍身上撒娇的阳光,背起背筐下了山。”“电话上的数字像奶奶喂的那群鸡崽,它们急不可耐地盯着小等的手,小等飞快地摁着,数字在她指下开心地咕咕叫。”“夕阳照着木屋,远远望去,屋子像一只橘黄色的老母鸡,温和地蹲在桂花坡山顶的林窝里。”“这不是奶奶干瘪的胸脯,也不是妈妈饱满的胸脯,它是河谷摊上一块被太阳烘热的大石头,硬而暖和。”
《暖》中这些语言扎根于黔北大地,贴近人物身份,既充满童趣,又形象生动。其中“甜滋滋,温嘟嘟,温和,暖和”这些词语,在语境中肆意地散发着温度,让人觉得“日子再难,都有温情的时刻;世界再冷,都有被阳光照耀的时刻。”表达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给人希望和力量。
阅读肖勤的作品,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气。”
【作者简介】

胡明琳,六盘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钟山区作家协会主席,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六盘水文学院签约作家。文字散见《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村金融时报》《贵州日报》《贵州作家》等报刊杂志。《皮匠二娃子》曾获贵州省“书香三八”征文一等奖。《商店人家》获贵州省作家协会与贵州省妇联联合举办的建党七十周年征文散文类三等奖。


